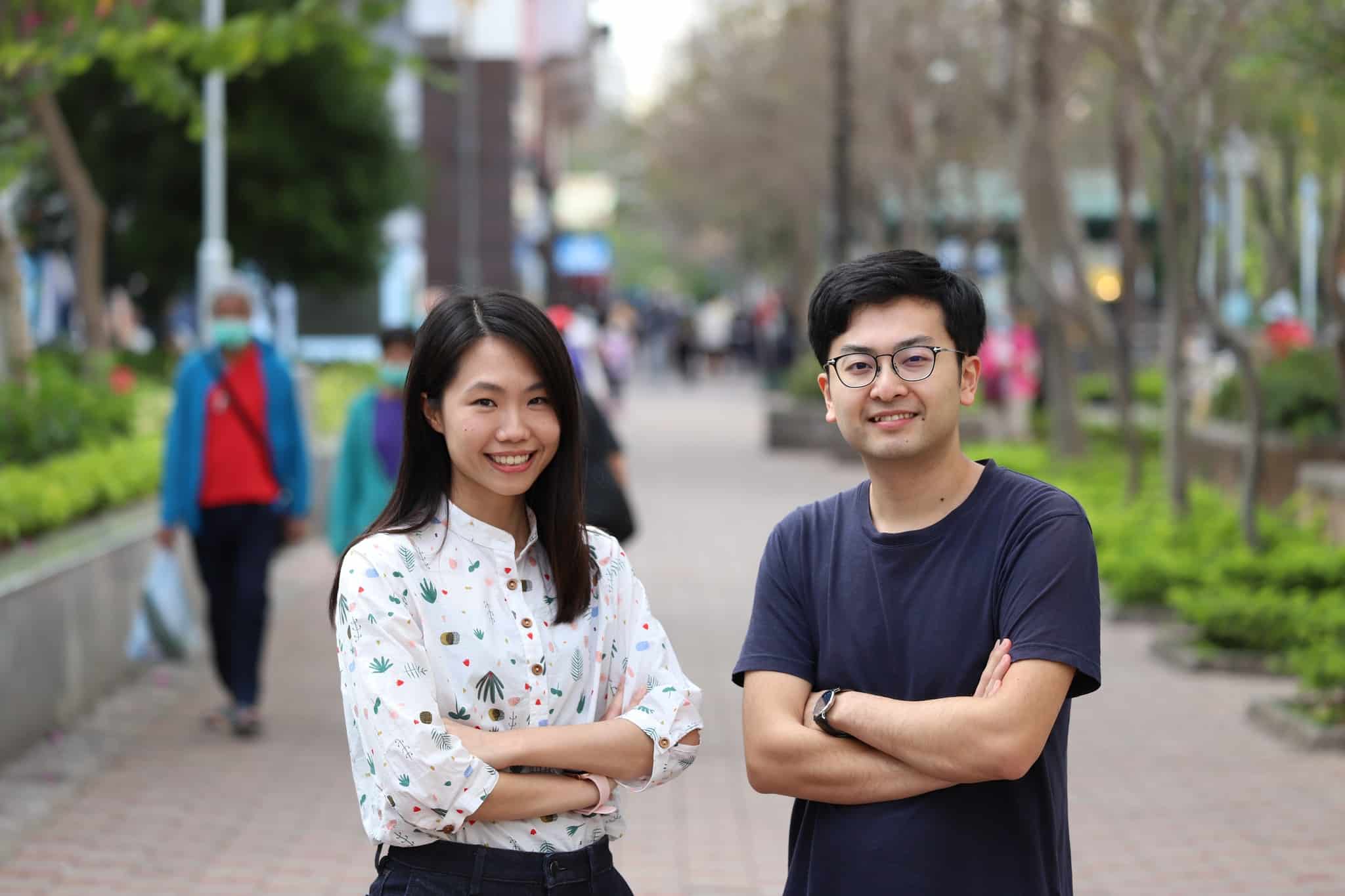近年香港有一種社區深耕細作的概念,有志者深入小社區,向普羅大眾作公民教育,再由下而上推動社會變革。2015年,阿柯和恩賜成立社區組織「天水圍人」,冀以自身能力為社會帶來一點改變。那天他倆坐在元朗一間咖啡店,談到改變社區:「大的事做不到,自己做小的事,看看在自己那一區能做到甚麼。」想起外國專頁「Humans of New York」,遂希望參考相關經驗,記錄社區的人和事,展開了「 天水圍人 Dialogues in Tin Shui Wai 」。
但大眾對天水圍的印象不就是悲情城市?曾當記者的阿柯道,以往做街訪時發現天水圍人相對熱情,比其他區街坊更容易展開對話。「可能本身我們時常周圍行和街坊聊天,有平台給他們講自己的故事。香港社會認定天水圍比較isolated(孤立),先不說悲情城市,而是一個較容易被忽略、邊緣的社區。我們希望讓外面的人聽到天水圍人的聲音。」阿柯說。
他們寫過不同天水圍人的故事:發現了「全港雜耍冠軍」等身懷絕技的街坊;也記下像毛公仔店那樣的小店故事——一轉眼,「天水圍人」已走入第五個年頭。
我們沿著輕鐵路軌旁走,從南到北,路上不少熟悉的面孔向他們揮手。行經一個輕鐵站,碰到昔日在天水圍北江賣毛公仔的伯伯。伯伯於年前撤出北江,三人久別重逢,聊起近況與往事,方知伯伯還未找到新舖落腳。言談間伯伯總是笑不攏嘴,街坊街里,簡單幾句噓寒問暖,人和人的連結是如此微小而強大。